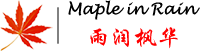谌旭彬
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谌旭彬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历史常识。但往往越常识的东西,越远离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商鞅,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家”,更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充其量,商鞅不过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正所谓:“商鞅不死,鲁难未已”。
▍其人:懂儒懂法懂兵,自身可能并无固定政治信仰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已不够详尽,目前可以知道的大略有: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卫是小国,不得不依附强大的魏国获取生存;商鞅成年后,投到魏国执政大臣公叔痤的门下,自称“卫国公孙”,因而也被世人称作公孙鞅或者卫鞅。商鞅,是他后来在秦国受封于商地后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由商鞅接替自己做执政大臣,并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应将其杀之。这恐怕不是史实,应该是商鞅入秦之后,为了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一套说法——因为公叔痤的推荐不合常理。其一,商鞅自己虽然很强调自己的“卫国公族”的出身,但其出身卑微是毋庸置疑的,西汉《盐铁论·非鞅》里很明确地说“夫商君起于布衣”,可见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再者,此时的商鞅,年不足30,职位不过是一介家臣,魏王此前更对其从未有所耳闻,公叔痤久历政治,岂能将这样一个人物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推荐给魏王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公叔痤临终前确实向魏王推荐了商鞅,但只是一种普通推荐,并没有让商鞅做自己接班人的意思。
公叔痤的死(公元前361年),让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需要寻找新工作的商鞅,想起了上一年(公元前362年)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的一道招聘启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遂决意去西方碰一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耗费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得以在公元前359年通过贿赂宫廷宠臣,见到秦孝王。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前后三次见秦孝王,先后谈了“帝道”、“王道”和“霸道”;前两次谈话秦孝王都很不满意,第三次才眉开眼笑。商鞅自己如此解释: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所谓“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大意是说按上古五帝三王的套路,需要三代的时间,才能完成帝王之业;秦孝王的意见,是要在自己生前“显名天下”,绝不愿再等上“数十百年”;于是商鞅换了一套“强国之术”推销给秦孝王,孝王大喜。
后世对商鞅这段话,有许多有趣的解读。如钱穆先生认为可以据此判断商鞅其实不是“法家”,而是一位“儒家”。因为他最先拿出来推销给秦王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秦王选择了法家的“霸道”之后,商鞅又感慨“难以比德于殷周”,所谓“殷周”,其实也是儒家(周公之治)。不过,这种解释,恐怕只是钱穆先生这类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商鞅确实拿儒家游说过秦王,但这并不能证明商鞅本人的思想皈依,因为商鞅同样也拿出了法家那一套东西,而且在日后运用得炉火纯青。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商鞅不过是在拿各种统治术迎合秦王罢了——儒家在当日虽很少有各国采用,但传播很广,商鞅能高谈“帝王之道”并不奇怪;何况商鞅本身所学就相当庞杂,除法家之外,他至少还是一位“兵家”,他的兵书,至少到西汉,还在广泛流传。
简而言之,如果秦孝王当日对“帝王之道”表现出浓厚兴趣,商鞅日后确实很可能会被归类到“儒家”范畴;但秦孝王当日选择了“霸道”,商鞅为个人政治前途计,遂成了“法家”的代言人;进而开启了一场反文明的“商鞅变法”。
▍其法一: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长期被有选择性地传播和有选择性地屏蔽。这种传播与屏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个长期被主流价值观所不齿的的“改革者”,和一场长期遭受历史谴责的“改革”,被彻底翻转。商鞅成了“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理论变成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这场改革变成了“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商鞅在秦国先后搞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见到秦孝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为“左庶长”,随即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秦国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动变法。前后两次的主旨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第一次变法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2、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3、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4、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按军功授爵这条规定,近百年以来,被称颂最多。或说它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或说它体现了某种公正、公平的原则,给了底层平民一个平等的上升通道。 这些效果,当然是有的。但在商鞅的本意,却并不关心这样的效果,他只不过想要将秦国改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秦国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诸侯称霸统一;秦国民众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给秦国这辆战车添砖加瓦。在《商君书·靳令》中,商鞅表达了一种“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的逻辑,原话是这样说的:
“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大意是:国家贫穷的话,一定要多搞战争,将毒害输送给敌人,本国没有“六虱”,国家一定强盛;国家富足的话,也一定要多发动战争,因为如果不发动战争,那么“六虱”就会在本国内部偷生,国家就会衰弱。换言之,就是国家穷,必须要多发动战争;国家富,也必须多发动战争;总之,国家要想强盛,一定要时刻保持一种战争状态,一定要时刻把所有资源,包括财力、物力、人力都牢牢地捆绑在战车上,如此,国家才能一直强盛下去。 至于什么是“六虱”呢?《商君书·靳令》也有详细描述,原话是这么说的: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原文如此)
在商鞅眼里,一切符合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标准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都是妨害国家强盛的“虱子”。
商鞅的变法令里没有讲“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也没有讲“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是国家强盛的死敌”,因为这些话不能明讲。但必须要了解到这些,才能了解到他大搞“军国主义”的逻辑。公元前的时代,当然还不存在什么“普世文明”,但为了国家强盛,连“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可以不要的变法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
▍其法二: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
除了“军国主义”之外,商鞅理想中的强国,还应该是一个遍地告密、人人互相监视的“特务国家”——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大意是: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某人犯法,其他人不去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而去告密的人则可以得到重赏——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特务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商鞅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逻辑。在《商君书·开塞》中,商鞅如此说道: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罪行发生之后,政府再对老百姓依法实施刑罚,并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老百姓自发产生义举之后,政府再出面奖赏老百姓,并不能起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的话,国家就要混乱。所以,统治者必须要在老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刑罚他们,如此就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要赏赐那些告密的老百姓,如此,则不过出现“细过”。统治老百姓,能够做到没有“大邪”、没有“细过”,如此,国家就大治了,就强盛了。天下就稳定了,“至德”就重建了。
最后,商鞅说了一句祸害历史数千年的话:“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以酷虐的杀戮,同样能够抵达“德义”。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告密”纳入国家体系并将其制度化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搞“事先惩罚犯罪”制度的人。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体制化的“事先惩罚犯罪”,蔓延了整个秦国乃至秦王朝,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孝文帝与众大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终于使得“告讦之俗易”,纠正了遍地告密的社会风气;所谓“罪疑者予民”,则非但不再有“事先惩罚犯罪”的制度存在,而且已经开始推行“疑罪从无”的理念了。汉文帝时代的刑罚制度,才真正“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商鞅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反文明的歪门邪道。
告密最终成为一种人人所不齿的行为,依赖于西汉之后,儒家意识形态的上升。苏轼讲过一个《神宗恶告讦》的故事,其中可以见到“禁止告密”的制度化:
元丰初年,开封府白马县发生盗案,有人知道谁是盗贼,但畏惧报复不敢直接告官,便向县衙投了封匿名信。后来盗贼被抓,捕贼的衙役争功,闹到上司那里,把匿名信事件引了出来,因为发生在京城,连皇帝也知道了。按宋朝的法律,告密是要被流放的,当时的开封府府尹苏颂认为出发点是为捕盗,惧怕报复也情有可原,上殿奏请对投匿名信者免予处罚。宋神宗却批示不准,理由是:“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最后的处理办法,是用板子打了投匿名信者的屁股之后,再给予一定的抚恤。
宋神宗的“严禁告密行为”,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才是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其法三:必须要“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初令付诸实施之后,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段文字,近百年以来,被作为商鞅变法“符合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进步”的证据,被各种各样地引用。《史记》的这段记载大体上应该是事实,理由如下:
1、在一个推行强制告密的特务社会,每个人都感觉处在他人监视的目光之中,行为必然谨小慎微,能够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并不奇怪。
2、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绝对的农本原则,《商君书·农战》里面说得非常明白:“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他的变法理论中,只有农业和战争,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其余职业都是多余的,都对国家强盛有害。这些多余的职业包括:知识分子、商贾、隐士、手工业者、游侠勇士。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被商鞅称作“五害”,成了改革过程中重点清除的对象。如此改革的结果,是全民从事农业,“家给人足”是必然之事。但同时造就了另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结构彻底单一化,一切有流动性的职业都从秦国消失了。“职业即原罪”,这是商鞅的伟大“发现”,被后世继承,带来灾难无数。
3、《史记》中所谓的“家给人足”,过于简单抽象,并不能完整反映商鞅时代秦国百姓的基本生存状况。实际上,这种“家给人足”,仅仅是一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的“家给人足”,而且这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正是商鞅所刻意谋求的。其变法理论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商君书·弱民》中说得明白: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赤裸裸地将“民”与“国”彻底对立起来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赤裸裸地宣称“强国之道在于尽最大可能剥削民众”的“改革家”。自西汉以来,儒家约束帝制,一直讲的是“民本”;近代以来,“民主”则已成世界大势——商鞅倒行逆施,竟能被歌颂成“符合历史潮流的伟大改革家”,真是奇哉怪也!当然,商鞅这套倒行逆施,也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其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商君书·弱民》)
这段话的大意是:老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国家就不能强盛。所以,老百姓富裕之后如果不主动消耗,就应该让他们拿出自己的粮食给国家(换取国家褒赏的爵位),如此,老百姓再度陷入贫穷,就会重新激发上进心,就不会偷懒,也不会“淫”,国家也不会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强上加强(“重强”)。
此处需要特别解释一下商鞅所谓的“淫”和“虱”。《商君书·外内篇》是如此解释“淫”的:
“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
什么是“淫”呢?商鞅说:“淫”就是“辩智”,就是“游宦”,就是“文学”,总而言之,“淫”就是谋取知识。商鞅理想中的治国之道,老百姓只能依靠农耕或者战争获取官职爵位;而“淫道”则提倡老百姓靠知识获取官爵名声——“辩智”、“游宦”、“文学”,是当时最主要的知识分子职业——像商鞅自己,依靠知识去游说秦王获取官职,就是典型的“淫道”。商鞅希望老百姓保持贫穷,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去追求“淫”,不会去追求知识,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威胁国家稳定的“虱”。
什么是“虱”呢?前文已经说过,“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商鞅把一切符合人类文明主流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都看成是妨害国家稳定和强盛的“虱子”。
这样的改革理论,怎么可以说是先进的呢?怎么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呢?难道说,“历史发展的潮流”,就是让老百姓保持贫穷,不让老百姓拥有知识吗?
将国家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彻底对立起来;鼓吹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让老百姓保持愚昧和贫穷,这是商鞅变法的理论核心,《商君书》中对此有大量不厌其烦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百姓的安居乐业,不是国家存在的理由;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成了国家的敌人。
“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民众越愚昧越容易治理,其前提是:国家的法律制定得很通俗明白,而且刑罚的执行力度很高。
“(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商君书·弱民)——“朴”是“淫”的反义,没有知识的意思——老百姓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老百姓弱,就安分守己,老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越志”)。商鞅在其变法理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民众越愚昧,国家越稳定,越容易治理;民众越弱,国家越强。这才是商鞅变法的真实理论逻辑。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如何才能让老百姓自发去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商鞅给出的答案是:光强制性地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在奖惩上积极引导,其具体措施就是:不要因为战功和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赐予任何官爵,尤其不要因为知识而给与官爵,如此久而久之,老百姓自然就会鄙视学问专心务农了;老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老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交流,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老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国家的大臣和士大夫们,不许去做任何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不许寄居他乡,不许施展自己的智巧,尤其不许到各县去居住活动,这样的话,老百姓就没有任何机会听到任何开启智慧的知识,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脱离农业;农民愚昧无知,不喜欢学问,就会一心一意务农。
商鞅所推行的,是彻彻底底的“愚民强国政策”。其彻底到何种程度,《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老百姓一开始反对变法初令,商鞅把他们抓起来排着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都变成了赤红色;十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老百姓倒转过来,称赞变法实实在在地好,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全家流放到边关。为什么在商鞅这里,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原因很简单: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他们只要会下田耕地、会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质,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反文明的变法,是中国历史的一颗毒瘤。
▍儒法之争的真相:“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
商鞅是法家的鼻祖。把商鞅的问题谈透了,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认识误区:法家是什么?儒家是什么?什么是“儒法之争”?
自西汉以来,古今的学者们就已经有一种共识,认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存在一条基本线索,就是“儒法之争”;长期以来,国体一直都是“儒表法里”,也就是以儒家政治理论为外表装饰,以法家政治理论为实际统治术。 这种论断,在近代以前的学者们的讨论中,本来是相当精准的。但不知为何,近代之后,学者们稀里糊涂,开始拿西方近代化过程中兴起的“法治”观念对应“法家”,进而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虽然学者们很谨慎地在区别着“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区别;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将法家的政治理念定义为“法治”,而只是谨慎地称赞其理念接近“法治”——但无论学者们如何谨慎,这些理解,统统还是都错了。
“儒法之争”的实质,不是什么“法治”与“德治”,而是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的问题。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是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商鞅大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乃是高举“以国为本”的大旗。孟子说“君视民如草芥,民当视君如寇仇”,乃是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商鞅大谈“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乃是高举“以国为本”的大旗。儒家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了家庭伦理,可以抛弃君主,这就是“以民为本”;商鞅则事事从国家利益出发,是典型的“国家至上主义”。
这种区别,古人本来是看得非常透彻的,“法家”和“法治”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的两码事——“法家”所谓的“法”,其制订者是单方面的当局,其制订时的立场,完全站在“国家利益”一侧,丝毫不为“老百姓利益”考虑;“法家”要老百姓遵守法律,是要老百姓无条件接受国家利益至上,无条件接受自身利益被国家“合法”盘剥;“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平等,“法家”的“法”里,岂能见到半个字的“平等”?
儒家在西汉之后势力上升,当局不得不将其吸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同样也重视制定法律,而且儒家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北宋宋神宗变法,搞出来一大串旨在增加国库收入的“新法”,儒臣司马光就非常愤怒,大声抗议“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不在民则在官”,痛骂朝廷通过变法“与民争利”——这是儒家搞法律的出发点,但从未见到有学者将儒家的这套法律治国理念,称作“法治”,也真是奇哉怪也!
把“法家”和“儒家”的基本概念搞清楚之后,“儒表法里”是什么意思,也就很容易明白了。汉宣帝对他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句话表达的,就是当政者热衷于搞“儒表法里”这套东西。“霸道”就是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王道”就是儒家的“民本主义”。商鞅愚民失败——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是商鞅愚民政策的继续而已,只不过商鞅当年在秦国小范围内能够成功愚民数十百年,但秦朝疆域包括其余战国群雄的领土,在那些国家,知识分子数量庞大而且活跃,那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能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秦始皇继续按照商鞅旧例焚书坑儒,就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了,其结果就是遗臭万年——早在西汉初年,知识分子就把焚书坑儒这个事情批判得臭不可闻——商鞅愚民失败的结果,就是此后的统治者不得不违心地接受“民本主义”的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其居于执政者的位置,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很自然地也会被其继承。只不过因为儒家强大的“民本主义”批判能力,“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数千年的暗流而不能见天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两千年“儒表法里”的真相。
将“法家”逼入地下,只能做不能说,是儒家两千年来对中国政治最大的贡献。两千年来,儒家始终坚持不懈地批判商鞅的变法逆流,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为例,与《史记·商君列传》相比,《资治通鉴》对商鞅及其变法的描述,做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更改。譬如:
1、《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已”;《资治通鉴》把这句话改成了“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2、《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秦本纪》也说:“法大用,秦人治”、“宗室多怨鞅”,还说:“居三年,秦人歌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改成“为政十年,秦人多怨”。
3、《史记·李斯列传》载有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中如此说道:“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至今治强”。《资治通鉴》则改成:“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删去了“民以殷盛”、“百姓乐用”等辞句。
很显然,司马光是在刻意地增加或者删改《史记》。其增删的指向非常明确:决不能让读者感受到“老百姓很支持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而应该是恰恰相反。司马光的这种增删,体现了一个信奉儒学的史家的细微用心——秦民在接受了数十百年的愚民、弱民、贫民改革之后,已然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史记》中所谓的“秦人歌之”,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真相。《资治通鉴》本是一部教给世人吸取历史教训的史书,司马光删掉“秦人歌之”,而增入“秦人多怨”,正是为了否定掉商鞅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
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
商鞅之术在中国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窒息。然而商鞅虽恶,却不过是迎合帝王。后代帝王并无商鞅,却用其术,这不是商鞅一个人的败坏,而是延续几千年的整体堕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历代治国者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认真回答这一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认知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说穿了,其实就是这一头一尾两场转型、剧变,前面这场“周秦之变”,是从周制走入秦制。而后面这场从1840年开始的剧变,其实关乎的就是如何走出帝制,或者说怎么走出秦制的变化。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