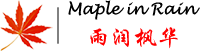秦晖

一个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解体后,原来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种秩序下重新调整“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建一种关系格局,这期间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会面临种种困境。
在世界历史上,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从未能避免这种悖论:一方面消除混乱是维持帝国、实行强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强力本身只能掩盖而不能消除致乱因素,以致于没有一个帝国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乱,恢复旧帝国也往往是永无可能。
于是“帝国后遗症”的结局多数都不外乎三者:
一是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社会情绪日益极端化,终于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旧式强力更严酷的强力控制。这种“乱世铁腕”可以在混乱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台。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帝国体制的解体,乱糟糟的“魏玛共和”维持了15年,终于使德国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绪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选上了台,并拥戴他建立了法西斯砖制的第三帝国。
与此同时“魏玛现象”遍及全欧,一战以来帝制解体后新生的许多共和国也纷纷抛弃“混乱的民-煮”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变方式产生了铁腕砖制,如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整顿”)政体与匈牙利的霍尔蒂独裁。俄国在沙俄倾覆后出现的“二月民-煮”也是如此:二月里上台执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无术失去民心,在民-煮选举的立陷会议上几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张“人民砖制”的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大获全胜。可以想见,即使布尔什维克不因大选失利而驱散议会,“二月民-煮”也极可能演变为铁腕砖制,只是砖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
第二种结局是帝国解体后的混乱发展为内战,而内战中民-煮自由秩序的生存机会更加渺茫,绝大多数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内战中的胜者建立新的铁腕控制,其最终结果与前述第一种结局一样,只是经过内战代价更大罢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从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的“分久必合,乱极生治”的王朝循环,直到1917年后的俄国内战、1911年后的中国内战。或者在内战中没有胜者,帝国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渐成为一盘散沙,最终不仅原先的“大国”不复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
后冷战时代这样的例子也俯拾皆是:从阿富汗、扎伊尔。南斯拉夫、索马里直到最近苏哈托垮台后的印尼――后者虽未发生全面的内战,但从东帝汶、亚齐之变直到各主要城市频频发生的暴力骚乱,也比前述那种“混乱的和平”无序得多了。至于历史上,从强力控制解体走向统一国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脱于这种命运的反是少数(中国在“治乱循环”中一直延续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罗马帝国解体后那样走向长期混乱乃至文明变异的却是世界历史上的“常规”。
第三种结局是外部输入民-煮与法治的新秩序,从而摆脱“砖制的稳定”与“混乱的民-煮”之循环,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德、日二战后在被占领状态下的民-煮化,二战后的西德没有步魏玛共和国的后尘,原因固然很多,二战后德国受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改造无疑是重要的一条。但这种状况要接受被占领的统治,除非出现非常条件(战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对于“帝国后遗症”有几点需指出:
第一,强力控制帝国的后遗症并不是某种“主义”所特有的,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强力控制由于过分地垄断社会组织资源,都可能导致社会缺乏替代组织能力,从而造成强力消失后的无序,出现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俄罗斯的“乱”被一些人指责为放弃了某种主义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认为某种“主义”要为如今的“乱”负责。
苏联帝国解体后产生一些与东欧国家不同的现象,与苏哈托砖制崩溃后印尼的混乱、1917年沙俄崩溃、1911年清帝国垮台后的混乱十分类似。它与帝国的意识形态无关。同时,乱中出现的新铁腕也非某种主义所特有,德国“魏玛共和”之后出现极右的纳粹砖制,俄国“二月民-煮”之后出现极左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体制产生于左翼——社会党,而匈牙利的霍尔蒂体制产生于右翼——箭十字党,但结束“混乱民-煮”,建立比旧体制更严酷的强权则是其共同点。
第二,这种后遗症也非某种“文化”所独有的。儒教的中国、东正教的俄国、天主教的匈牙利与新教的德国都出现过这种现象,而且不但像中、俄这样砖制帝国历史悠久的国家出现过,经历过启蒙运动深度洗礼并久已实行立陷制度的德国出现过,甚至在中世纪就长期具有“贵族民-煮”、“自由选王”等非砖制传统的波兰也出现过萨纳齐砖制这样的现象。当然,传统可能使人更能适应某种体制,但造成帝国后遗症的一些基本因果关系(组织资源垄断与无序状态的互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第三,外界的干预并非这种后遗症的基本原因。有些国家如后蒙博托时代的刚果(金)、后殖民时代的安哥拉出现乱世,固然与外因有关,但大多数国家,如西亚德之后的索马里、门格斯图之后的埃塞俄比亚、苏军撤走后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乱因素都主要是内因。在有些场合外来干预反有助于稳定,如国际社会的监督对南非过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无论外因是促进稳定还是生乱,都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
第四,“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固然前行道路荆棘密布,虽偶有倒退,但回到昔日的可能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D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混乱中产生新强权、更严厉的强权是很可能的,但恢复旧式强权则罕有其例。
就连俄罗斯这种民族性和帝国性特征密切关联的国家,据说俄属于“染色体分析”帝国构造形式鲜明的国家,至今很多俄罗斯人仍迷失在“我们祖上曾经阔过(帝国的疆界)”的臆想中无法自拔,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81.9%粮食出口增长来源于18世纪扩张的7个草原省份,他们把帝国扩张的红利看成是历史上的“黄金年代”。连这类国家都无法向“帝国退化”,更遑论他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