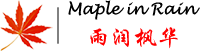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亿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不久前,当李克强总理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表示瞠目。
6亿人?1000元?
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猪肉。
这怎么可能?!
说实话 ,当我听到这句话,却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
注意,1500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
而这些人在哪呢?
就在中国经济的最强省——广东。
1
广东的两副面孔
有人说,广东富得流油。
这话我没法反驳。
毕竟自1989年起,广东已连续30年稳坐各省GDP总量第一的宝座。
“万年老二”的江苏,一直喊着要超过广东,但结果呢?
去年广东依然第一,江苏还是老二。
2019年,广东的经济总量超10万亿人民币,与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总量相当。
说广东“富可敌国”,真不是吹的。
但作为一个在广东待了20年的人,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很清楚,广东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广佛莞惠珠,富的是马化腾许家印杨惠妍;
而不是粤西粤东粤北,不是地里的农民、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是写字楼里的基层白领。
所以我常常说,广东有两副面孔:
一面富可敌国,一面穷得离谱。
早在1988年,据说在一场全国的贫困地区经验交流会上,广东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灵魂拷问:
“广东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广东这么富,还来参加穷人的会议?”
22年后,我又听到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谁敢说这话?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而且这是2010年他在广东河源调研时,当着记者的面说的。
这句话还引发了一波讨论。
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的富,却很难相信它的穷。
但对于这句话,我也没有多意外。
几年前为了见一位故友,我从深圳开车到湛江,不到10小时的车程,沿路的风光却堪称当代中国经济地域差异的缩影。
从深圳出发,途经广州、佛山、中山、肇庆;再往西,便是云浮、阳江、茂名……
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到厂房和烟囱遍布的工业地带,再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萧条的村庄。
这就是这一路变化的风景。
唐朝诗人孟郊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我想说的却是:秋风萧瑟马蹄疾,一路粤尽富与贫。▲广东韶关
确实是这样,广东的确是全国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省。
举个例子:
2019年,广东最富的是深圳,最穷的是云浮,前者的GDP是后者的多少倍呢?
29倍。
而“万年老二”的江苏,它最富的是苏州,最穷的是宿迁,而前者的GDP只是后者的6.2倍。
同样,在排名第三的山东省,最富的青岛和最穷的枣庄之间,GDP的差距也只有6.9倍。
广东各区域间的贫富分化,远甚于其他省。
再具体到每个人,广东的贫富差距更超乎想象。
比如说,每年的全国胡润百富榜,广东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数稳列全国各省第一名。
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仅前10名广东就占了整整6名。
但与此同时,截止到2018年,广东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13个省级特困县,12个山区贫困县。
在广东这片被誉为“遍地黄金”的土地上,还有很多人依旧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甚至无处容身。
2
地上有金子,他们却看不见
2010年,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组,曾深入到粤北地区进行采访。
随后,他们推出一期名为《“穷广东”调查》的节目,其口号是:
“颠覆一个熟悉的富广东,重建一个没有贫穷的新广东。”
广东到底有多“贫穷”呢?
在节目中,一位村民告诉主持人:
三餐都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喝粥就不会饿。
另一位村民则告诉记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家的年收入是几千块。
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出去,结果那时连洗衣粉也买不起,孩子发烧了还得向别人借钱。
还有一户村民,他家里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饭、吃饭、住,都在里面。
四壁熏得乌黑,没有像样的家具,铺盖、卧具又黑又硬。
看着这番情景,当时韶关市社会保障局的刘海翔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感慨道:“没想到城市差距会那么大,改革开放都30年了。”▲广东韶关
当年,《南方日报》也做了一系列关于《“穷广东”调查》的报道。
他们派出7位记者,分赴7个贫困村驻村采访,涵盖了粤东、西、北,甚至还有一个村子就在珠三角。
比如说,在粤西的雷州,东塘村的村干部就自嘲道:“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
由于土地贫瘠,沙化严重,雨季有积水,旱季有时又长时间滴雨未下,这里的粮食亩产量最多只有500斤。
而在其它地区,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当时东塘村有3957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2021人,贫困率超过51%。
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依然没有厕所,学生想上厕所只能到学校附近的树林解决。
时间一久,树林里臭烘烘。
“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
由于条件艰苦,师资力量匮乏,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
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于是“雷州普通话”便代代相传。▲ 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等上了中学,每学期200元的寄宿费和每星期20元的伙食费,又成了村民们沉重的负担。
村支书王南介绍,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130人就读初中,但其中超过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
校长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鸿沟”。
但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果不其然,一批批从东塘走出去的年轻人,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又铩羽而归。
他们接过父辈的锄头,结婚生子,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
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实在是太难了。
3
“民工荒”
当张五常说“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当粤港澳大湾区高喊着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群。
粤西粤东粤北的贫穷,似乎显得“不合时宜”。
有人说,珠三角明明出现了“民工荒”,为什么还有人窝在村里挨饿?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大约是从2004年,我们开始频繁地从媒体上看到3个字——“民工荒”。
紧接着,很多学者也说“刘易斯拐点”要来了。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业转移时,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形成,城乡收入也将趋于平衡。
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
不妨做个对比。
2009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9亿,占总数的38.1%。
而2010年,美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仅为0.7%,加拿大为2.0%,日本为4%。
中国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还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而在这2.9亿人当中,还有一亿多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
所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来,这是个假“拐点”。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
于是, “民工荒”和“贫困的农民”同时出现,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论。
但再一琢磨,却发现并不矛盾。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工厂都缺工人。
据2011年的一项数据统计,那些雇工难的企业所提供的工资更低,而且工作时间更长,福利条件也更差。
如果企业平均月工资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基本不会缺工。
月收入1800元是什么概念呢?
当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较为便宜的农民房,比如说在拆迁之前的白石洲,一间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800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说也要一千多。
而当时农民工的平均月薪,却只有1521.14元。 ▲深圳非熟练农民工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一个人背井离乡,假如他的工资只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无法保证基本生活,他还愿意外出务工吗?
显然不愿意。
于是就出现了“民工荒”。
所以,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缺少劳动力,而是企业缺钱(当然,也有农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问题)。
《南方周末》的记者曾在广东采访了一个鞋厂,该厂老板说:制鞋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
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早在200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东莞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东南亚。
之后,这种现象很快像瘟疫一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蔓延开来。
企业之所以选择搬迁到东南亚,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
换言之,他们嫌我们的农民工还不够廉价。
农民工和企业主,到底孰对孰错?
无法断言。我只能说:各有各的苦。 ▲专门记录打工族的影片《我的诗篇》
4
“先富”如何带动“后富”?
疫情期间,有位揭阳的读者向我诉苦。
他说以前常常私底下骂老板,骂工厂,骂“万恶的资本家”。
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作实在是辛苦而乏味,没有前途,工资还低得离谱。
而今年因为疫情,工厂迟迟没有复工的消息。
他开始怀念起流水线上的日子,因为至少那时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我问了他近期的打算,却没敢问他将来的梦想。
因为“梦想”对他而言,也许太过虚无和沉重。
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年轻人——“打工诗人”许立志。
2014年,他在富士康坠楼身亡。
这位敏感而有才华的年轻人,也来自于粤东地区的揭阳。
那里贫穷落后,为了生存,为了梦想,大量的人来到珠三角打拼。
在那首《我就那样站着入睡》中,许立志这样写道:
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不会控诉,不会埋怨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赐我以迟到的安慰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拒绝迟到,拒绝早退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其实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因为“11连跳”事件而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工人的嘴里,这里冷漠、压抑,工人们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影片《我的诗篇》
人们嘴里虽然抱怨,却仍前赴后继地涌入这个“没有感情的制造工厂”。
因为这里的工资,比别处更高。
这就是现实。
前些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北上广容不下肉身,老家放不下灵魂。
这显然是出自都市白领之口,因为他们回到家乡只能当老师,当公务员,然后朝九晚五混吃等死。
但换做是农民工,他们大概会说:北上广容不下的肉身,老家同样容不下。
因为回到家乡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有一块荒芜的土地。
他们连当老师当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
现实告诉他们,饿着肚子的人,还不配谈论“灵魂”。 ▲影片《我的诗篇》
还有一点颇值得玩味:
在广东,“村民”这个词被赋予了两种含义,分别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一种“村民”住在韶关的梅花村、清远的大成村、雷州的东塘村……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过得捉襟见肘。
另一种“村民”住在广州的猎德村、深圳的岗厦村……
他们可能趿着拖鞋,穿着汗衫,腰间别着一串钥匙,每月定期收着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轻轻松松月入几万,甚至几十万。
他们是广东的“隐形富豪”。
当后者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一骑绝尘,而前者却仿佛被时代遗忘,他们成了大时代下“掉了队”的人。
而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强者恒强,弱者更弱。
当广州猎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东塘村的“农二代”相遇,这种“鸿沟”会更加明显。
2010年,当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组深入到粤北地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他是这样设计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面半句话,我们政府是很有经验了,怎么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小平同志后面那句更长的话,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视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远不只是一句“忽视”那么简单。
作为一名小小的作家,我并不能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只能借此文章,展示一些实像。
你可能会说我不够正能量,我却想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弘扬正能量,也不差我一个吧?
因为,世界很少把聚光灯打给那些掉队的人,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就不存在。
就像贾樟柯所说: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