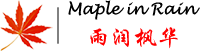说起著名学者,我的感觉,美国学者比中国学者,在一般社交意义上要好打交道。
这不是道德评价,而是一个事实和文化差异——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有一种统一的,彬彬有礼的 manner 。
即使你只是不小心闯进了他的办公室,也会收获一场愉快的对话,即使过后都忘记对方,但面对面的时候,都想留给别人一个温和有礼的印象。
和陌生人友善地交往,总能找出合适得体的话题来聊,是西方文化里的好的一面。
还有一些美国著名学者,确实也是古道热肠,爱帮忙。
中国学者中的现在年龄六十多岁的,基本上已经达到学术巅峰,甚至也熟练掌握外语,对西方不算陌生,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美国人的那种在我看来必要的manner。
比如,我做一个报告的时候,被一个国内著名学者当众大声教训——你这个中文理解都是错的,英文翻译过来就更…云云。其实,我的理解和翻译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糟糕,他也没有具体指明什么地方错了,但是这种当众让人下不来台的表达,说明这位学者本质上就个人的修养来说,不经意就流露出傲慢和粗鲁。
我不是说不可以提意见,但是提意见有很多方式,比如委婉地私下提,或者先想想他自己的那个否定是否公正,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同一位学者,在另一场活动中,当有人提到一个什么公认为经典的,也是断然地评论:这个XX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价值!语气似乎从来都是不由分说,然而事实却也绝非如此。以他的影响力,会不会真的有人从此怀疑这部典籍的价值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美国学者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论断任何一个研究对象没有价值。
还有一位学者,是在私下场合了,直接劈头一句——你怎么连这个人都不知道啊?其实也许就是一时没听清。我也不客气了,当场反击,张老师,您的观点其实我并不同意。
还不必说那些在会议进行中大剌剌接听手机的“著名学者”。
有的在美国的华裔学者–成年以后从大陆去的——开会的时候见面会从头到脚地打量人,或者斜着眼看你。
在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交的论文所收到的所有批评和否定,包括那种轻浮和嘲弄的语气都来自中国学者,而所有的肯定和鼓励都在会后来自美国/加拿大学者,而且并不是假客气(我并不记得他们在现场,他们可以只打招呼不必再评价已经过去了的论文内容),还有很认真地讨论细节的,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佐证–至少说明这名已经从哈佛退休的美国老学者是认真地去思考过的,尽管他以前可能也没有想过。这篇文章最终顺利地发表出来–他们的肯定是我继续修改的动力之一。
那么,那些自诩为权威的学者是不是否定得过于仓促和自负了?我甚至在想,要不要把这个轻薄之徒的名字点出来?
还有一位台湾学者,八十多岁了,接触起来也是真有洵洵儒者之风。
国内学者没有学会积极地鼓励一个人。
他们似乎只习惯两种表达:不认识你,就拼命攻击贬低,如果是他们自己的人, 就拼命吹捧。
当我们在空谈创新,“世界一流”的时候,夸美国人如何“新见迭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多少尚不成熟,但完全有潜力的新见,已经被这些粗暴武断,动不动就居高临下否定别人的学阀打击了,只容许在原有框架里做点考据,或者把过世的偶像年年纪念岁岁研讨。
“世界一流”的教育不是这样的。
好的教育要求处在权威地位的人保持开放和平等的心态,不要轻易否定任何人,也不盲目造神,因此,在美国的教育中才一直都有“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问题” 这种尊重和思考他人的角度的理念。
总之,国内一些学者本人也许不坏–我也愿意与人为善–但表达过于直白武断,欠缺西方学者,或者明显温和谦逊很多的台湾学者那种涵养(这是个人修养问题),和思考自己可能不习惯的观点的气度,而且本能地否定,甚至断然否定所有自己不习惯的角度和观点(这是对待知识的态度问题,但和个人修养不能说完全无关)。
很遗憾,我确实常常提出他们没有想过的东西,而且认为他们最终会理解。我觉得这种区别是很明显的,但背后的原因也就不必深究了。
我可以说这个话,还因为我自己鼓励和直接帮助过一个在别人眼里毫无价值的研究,直到这个研究最后以SSCI论文发表出来。如果我打击这个作者,这篇文章可能不会有进一步做下去的希望。
我希望我自己对待每一个学问的同道中人都首先尊重和正面看待别人认真和经过思考以后说出来的东西,加以思考。可以在论证上提出商议和补充,或者闭嘴,但在论点和角度上一棍子打死是非常不利于新见出现的。
也希望更年轻的学子能注意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观点,但在对待他人方面有一种开放,温和,理智,包容的态度,不要去追求盛气凌人的气势,把学术圈搞得那么吓人,不要在无形中已经学会了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