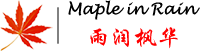—— Parscal
当地时间2009年3月6日晚间10时49分,一枚液氧煤油动力的火箭搭载着一台科学观测设备进入了太空。此枚火箭从距一颗G型恒星第三近的行星上发射,该恒星距离银河系中心25000光年,而银河系自身位于处女座星系团的边缘。发射当晚,天空澄澈,无雨无风,按绝对温标计算,气温为292度。当地的智慧生命为这次发射欢呼。在发射前不久,负责宇宙飞船的政府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全球计算机网络上写道:“我们期待着精彩绚烂的一夜,届时开普勒空间望远镜将发射升空,它的任务是致力于搜寻太阳系外的类地行星,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一粒沙:戈壁滩的面积达50万平方英里。如果用它来代表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那么生命物质就仅仅相当于一粒沙。
上面这段叙述也许会由某颗遥远行星上的智慧生命写下,而这类行星恰好就是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搜寻目标。这架望远镜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名字命名,专门用来寻找太阳系外的“宜居”(habitable)行星——也就是说,它们离中央恒星的距离既不会太近,致使水被蒸发掉,也不会太远,这样水不至于结冰。大多数生物学家认为液态水是生命存在的先决条件,哪怕它们与地球上的生命形式非常不同,这一条件仍是必须。开普勒望远镜已经调查了银河系中的大约15万个和太阳系类似的恒星系统,并发现了超过1000个外行星。它收集到的庞大数据至今仍在分析中。
如果戈壁滩代表了宇宙中飞掠的一切物质,那么生命物质仅仅是一粒沙。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人类一直推测,宇宙其他地方可能存在生命,乃至普遍存在生命。而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能尝试回答这个深刻的问题。就目前而言,从开普勒任务的结果可以推断出,大约10%的恒星拥有一颗绕其运行的宜居行星。这个比例是巨大的。仅在我们生活的银河系中就有1000亿颗恒星,而河外还有无数星系,因此,很可能还有许多、许多存在生命的太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 Syfy Wire
然而,还有一种更宏大的观点认为,生命在宇宙中是罕见的。这种观点将所有的物质形式都考虑在内,包括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即使所有(由开普勒望远镜确定的)“宜居”行星都确实存在生命,宇宙的所有物质中有生命的部分所占的比例仍然是非常小的。假设地球上有生命的那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生物圈(bioshpere)——在地球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和其它有生命存在的行星情况类似,那么据我估计,宇宙中一切生命物质的占比大约只有十亿分之一的十亿分之一。有一种方法可以形象地表现这么细微的比例:如果戈壁滩代表了宇宙中飞掠的一切物质,那么生命物质仅仅是这片沙漠中的一粒沙。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生命的这种极度稀有性呢?纵观人类历史,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类自身和其他生命形式包含着某种特殊的、非物质的本质,这种本质是非生命物质所不具有的,并且遵循着与非生命物质不同的运作原理。这种观念被称为“活力论”(vitalism)。
© Church Life Journal/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活力论者。笛卡尔是活力论者。19世纪的现代化学之父约恩斯·雅各布·贝采里乌斯(Jöns Jakob Berzeliusbb)也是活力论者。这种假想的非物质的生命本质,特别是在人类体内的这种本质,有时被称为“精神”(spirit),有时则被叫做“灵魂”(soul)。公元前8世纪的古埃及皇室官员库特姆瓦(Kuttamuwa)建造了一座重达800磅的纪念碑以供他不朽的灵魂住宿,还要求他的朋友们于他肉身故去后在那里设宴,以纪念他的来世。10世纪的波斯博学家阿维森纳(Avicenna)认为,哪怕在一切外部感官输入都切断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进行思考、保有自我意识,既然如此,我们的体内一定存在着某种非物质的灵魂。这些都是活力论的观点。现代生物学对活力论发起了挑战。1828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Friedrich Wöhler)用无机化学物合成了有机物尿素。尿素是许多生物体新陈代谢的副产品,在维勒之前,人们认为尿素只与生命体有关。到了19世纪晚期,德国生理学家马克斯·鲁布纳(Max Rubner)证明,人类在运动、呼吸和其他形式的活动中消耗的能量,正好等于所消耗的食物中含有的能量。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隐藏的、非物质的能源来为人类提供动力。近年来,蛋白质、荷尔蒙、脑细胞和基因的结构已经被拆解到原子层面,仍旧没有发现非物质存在的迹象。© Los Angeles Times然而,我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对此是否有意识——仍然是潜在的活力论者。尽管有时候我们躯体的物质属性会向我们大声尖叫,昭告自身的存在(比如当我们肌肉受伤或是用精神类药物调节自身情绪时),但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它似乎源自一种不同的存在,一种非物质的存在。知觉、思想和自我意识这些感觉是如此摄人,如此直接而宏大,以至于我们难以相信,它们仅仅来自我们大脑中细胞所产生的电子和化学刺激。然而,神经系统科学家说,事实的确如此。
一个没有评注的宇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
美国公众的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人相信生命在死后仍以某种形式存在。这种观念当然也是一种活力论。如果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不过是由物质原子构成的,那么,正如卢克莱修(Lucretius)在两千年前所写的那样,当这些原子在人死后消散时,生命就会不复存在。矛盾的是,如果我们能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蕴含着某种超验的、非物质的本质,如果我们能接受“自身纯然由物质构成”这种观念,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新的特殊性,它足以取代“活力论”所赋予我们的特殊性:我们是特殊的物质。我们人类生活在这颗星球上,总是为人生之短暂和肉体凡胎的限制而苦恼烦忧,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活着本身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在宇宙间那不计其数的原子和分子中,有极其稀少的一部分按特殊的排列构成了生命物质,而我们有幸从这其中脱胎而出。我们是那十亿分之一的十亿分之一。我们是沙漠中的一粒沙。那么这种被称为“生命”的特殊排列又是什么呢?是在有机体周围形成一层外膜,将它与外部世界隔开的能力。是在有机体内部将物质组织起来并进行一系列过程的能力。是从外部世界中提取能量的能力。是对外部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的能力。是维持有机体内部稳定的能力。是成长的能力。是繁殖的能力。我们人类无疑拥有这些特性中的一切,甚至更多,因为我们体内有数以十亿计的神经元相互连接,形成了一幅由交流和反馈回路构成的精美“织锦”。我们拥有知觉和自我意识。© Literary Ocean
在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中,两个流浪汉被置于一座既无明确时间也无明确地点的极简主义舞台上,无休止地等待着神秘的戈多,刻画出了我们对存在之意义的困惑。
爱斯特拉贡(Estragon):“我们昨天做什么了?”弗拉第米尔(Vladimir):“我们昨天做什么了?”爱斯特拉贡:“是啊。”弗拉第米尔:“我的天……(愤怒地)只要你在这,就什么也没法确定。”
当然,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惯性思维,如果我们的宇宙观能够有所超越,达到真正让人深思费解的层次,就能发现另一种看待存在的方式。我们不仅是有生命的物质,更是有意识的物质,我们拥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成了宇宙的“观察者”。我们对自己和周围的宇宙都有独特的感知。我们能够观看,能够记录。我们是宇宙评注自己的唯一机制。其他的一切,这片沙漠中其他每一粒沙,都是默然而无生命的物质。当然,宇宙不需要对自己做出评论注解。完全没有生命物质的宇宙也可以顺畅地运转——它能无意识地遵循能量守恒、因果关系和其他物理定律。宇宙根本不需要思想,也不需要任何生命物质。(诚然,在近来许多物理学家支持的“多元宇宙”假说中,绝大多数的宇宙里是完全没有生命的。)但是在笔者看来,一个没有评注的宇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人曰瀑布美矣、山美矣,此言何意?“美”这一概念,以致于所有的价值和意义的概念,都需要观察者才能成立。如果没有意识进行观察,瀑布便只是瀑布,山也只是山。正是我们这些有意识的物质——所有物质形式中最稀有的物质——才能审视、记录面前这一整个宇宙的存在,才能宣称这些存在之存在。我意识到上述这段评论中存在着部分循环论证。这是因为,“意义”也许只有在思想和智能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如果思想不存在,那么意义也不存在。然而,事实是,我们的确存在。我们有思想。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物理学家们或许会构想数十亿个没有行星、恒星或生命体的自洽宇宙,但我们不应忽视我们自己的平凡宇宙和我们自身存在的事实。纵使我认为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只不过是原子和分子这些物质,但我们业已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意义之宇宙。我们建立社会。我们创造价值。我们构筑城市。我们发展科学和艺术。自人类记下历史的第一笔以来,我们一直在这么做。
英国哲学家科林·麦金(Colin McGinn)在他的《神秘的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1999)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可能理解意识现象,因为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的思维去讨论它。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困在神经元网络中,而我们试图分析的正是这张网络产生的神秘体验。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被禁锢在自己的意义之宇宙中。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我们不一定是在谈论某种宏大的宇宙意义,或是某种上帝赋予的神圣意义,甚或是某种长存、永恒的意义。我们谈论的也许只是寻常点滴、转瞬即逝的事件,比如湖面上一闪而过的波光,或是一个婴孩的出生,我们谈论它们那简单、具体的意义。无论是好是坏,意义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的一部分。鉴于我们已然存在,我们的宇宙必须有意义,不论是宏大还是渺小。虽然我还不曾在地球之外的广袤宇宙中遇见其他生命,但我相信它们都拥有智能,若非如此,我会很惊讶的。我还相信,这些智慧生命和人类一样发展科学和艺术,并试图审视、记录这一整个宇宙的存在,若非如此,我会更加惊讶的。我们与这些生命体共享的并非活力论那神秘、超验的本质,而是生命本身这一罕见至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