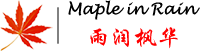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送别》是李叔同在1914年创作,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李叔同的大名,但是这首歌却大都听过,唱过。
歌词属婉约一派,清新淡雅,情真意挚,凄美柔婉,其中画意诗情,更是相得益彰。历经百年时光,依然是送别诗中的不二经典。
李叔同出生于1888年,家里经营盐业和钱庄,是天津巨富。
他的前半生是风情才子,后半生是却是世外高僧。
在中国百年的文化史中,李叔同是公认的通才和奇才。
无论音乐、戏剧、书法、绘画、诗词皆是一流,堪称全才大师,中国现代艺术的鼻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艺术巨匠。
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最早将油画、钢琴、话剧引入中国,
擅长书法、诗词、丹青、音律、金石,在当时是整个学术界神一般的存在。
我们熟知的漫画大家丰子恺先生,就是李叔同的得意弟子。
但是在盛名抵达巅峰之际,他却选择抛妻弃子,遁入空门,从此苦修半生,留给世人难以揣测的玄迷。
李叔同父亲是清朝同治四年的进士,曾经是吏部主事,后来子承父业成为津门巨富。
在李叔同五岁那年,父亲去世,让幼小的李叔同过早地见识到了生离死别。身在富贵之家,却时有世事无常的幻灭之感。
加上李叔同为家中庶子,父亲去世之后,身份尴尬,因此自小便生性敏感,寡言少语。
他在15岁读《左传》《汉史精华录》时候,就曾写下“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句子。
在少年李叔同的心中,已有了对人世繁华苍凉的思考,因此对先生教授的“正业”也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当时的“贱业”唱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戏曲里的人生百态对年幼早熟的李叔同而言,无疑更有吸引力。
李叔同当时十分喜欢伶人杨翠喜,天天去戏园捧场,本是少年人的情窦初开,奈何,杨翠喜后来被卖给官家,而李叔同也奉母命,迎娶茶商之女。
感情不顺,李叔同对家事更是不再上心,哥哥给他30万元让他安家置业,他把这笔巨款也多半花在了艺术上。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有志之士无不渴望变革图强,维新变法兴起之时,李叔同热情高涨,刻下印章“南海康梁是吾师”,四处宣扬变法。
谁曾料想,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竟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一百多天。
眼见才刚刚得势的维新党人死的死,逃的逃,世事无常的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李叔同那颗敏感的心上。
于是李叔同效法柳永,在茶馆酒楼之间,纵情声色,逃避现实。他家底殷实,出手阔绰,和很多的文人名妓都有往来。在20岁的时候,他搬到许幻园家“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极具纨绔之风。
就是在这烟花柳巷,声色犬马的几年,让他对这些在红尘中摸爬滚打的伶人戏子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知道他们精致生活下的逢场作戏,见到过他们朝夕之间的绚烂与黯淡,也见过这其中的荒唐与苟且。
25岁的时候,李叔同再遭变故,他年仅46岁的母亲撒手人寰。安葬完母亲之后,他极为失落。颓丧之际,他远走日本,在日本的学校里专攻美术,辅修音乐。在日期间,他还专门雇日本女子做模特,随后与她产生感情,结为夫妇。
此外,他还自编音乐杂志,传播西方乐理,推广作曲方法。归国之后,李叔同投身教育,力求开启民智,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
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叔同常常一人写诗作画,对于人生超常的体悟,以及对艺术的天分,让他很快脱胎换骨,与以前的“纨绔子弟”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在艺术上的高度,让他知音寥寥,他在浙江甚是孤寂。
一日,好友拜访,李叔同陪伴友人谈天说地,写诗论画,心情畅快。
在好友离别之后,李叔同心中惆怅,写下了著名的《送别》,一句“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让飘零、无常跃然纸上。
父母早亡,生性敏感,加上早熟的思悟,让李叔同过早地看到了人世间的无常与悲苦,
他希望借助艺术,来安抚内心的痛苦,但却屡屡不得。
在偶然的情况下,李叔同接触到了佛家的苦修之法,他断食二十天之后,认定佛教才是自己的心灵皈依之所,决定出家。
1918年6月30日晚,李叔同正式出家,不是带发修行的居士,而是入山苦修。他只带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其他一概不带。
学生问他:“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剃度几个星期后,他的日本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杭州灵隐寺,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劝说丈夫切莫弃她出家。这一年,是两人相识后的第11年。然而叔同决心已定,连寺门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他的妻子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与他见最后一面。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
李叔同的日本妻子:“叔同——”
李叔同:“请叫我弘一”。
妻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很多人谩骂李叔同,说他抛家弃子,不负责任云云,然而在出家之前,他曾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将其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先生,转交给自己的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将妻子送回日本。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弘一大师内心的柔情和歉疚以及处事的细心和周到。
学生刘志平,留学日本时经济十分困难。李叔同私下资助这位学生,薪金微薄的他每月坚持寄钱,不求其偿还,并叮嘱不可告诉他人,直至刘志平学成才停止资助。
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算无情?
有这样一个故事,
佛招弟子,应试者有三人,一个太监,一个嫖客,一个疯子。
佛首先考问太监:“诸色皆空,你知道么?”
太监跪答:“晓得。学生从不近女色。”
佛一摆手:“不近诸色,怎知色空?”
佛又考问嫖客:“悟者不迷,你知道么?”
嫖客喜笑颜开答:“知道,学生享尽天下女色,可对哪个婊子都不迷恋。”
佛一皱眉:“不留恋,哪来觉醒?”
最后轮到疯子了。佛微睁慧眼,并不提问,只是慈爱地看着他。
疯子捶胸顿足,凄声哭喊:“我爱!我爱!”
佛双手合十:“善哉,善哉。”
佛收容疯子做弟子,开启他的佛性,终于使他成了正果。
李叔同有太多的爱,他对人世有太多的眷恋,他爱妻儿、爱学生、爱艺术、爱朋友,爱人世间的每一个人,可他又早已看破无常,他知道所深爱的都将逝去,他的眷恋越深,折磨愈甚。
他的学生丰子恺曾经说过,人生有三种境界,物质、精神、灵魂,生活在物质层次的人,只要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
其次,高兴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而李叔同,恰恰属于第三种。
艺术已经不足以安放他的心灵,所以,他选择了宗教,以此来超越无常的苦痛。
亦如李叔同对他的妻子所言,爱是什么?是慈悲。
众生皆苦,生老病死,爱憎会,恨别离,求不得,放不下。
而佛,便是舍弃个人的爱恨,普度众生的痛苦。
为弘扬佛法,他置生死于不顾。1937年底,厦门轰炸不断,众人劝他避难,他却集众演讲,尽一己之力,渡劫众生。
每次开讲时,后面的墙壁上,都挂着他亲手书写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在弘一法师看来,以佛之觉悟普度众生,激励僧俗两界一同奋起救国,即便牺牲一切,舍命不辞。
因为放下了个人的爱恨,也就回避了无常的悲苦,了悟小爱的无常,也便成就了大爱的慈悲。
在这世事变幻中,内心才能不被煎熬,以此获得安宁。
李白曾经写过“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所有的有情,有一天都会变成无情,因为来生我们都只能在虚无缥缈的银河再会。
蒋勋也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一种是生离,一种是死别。
若是要摆脱其中的痛苦,就要学着放下,放下执着,学会超脱,放下小爱,学会大爱。而唯有这样,人生才得从容。
就像弘一法师去世之前,写给自己弟子诗里的那句: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春满花开,皓月当空,心中一片宁静安详。